林玉体博士、教授、院長當然是一位學者,但是這本書以學者的立場寫下的文字並不顯著, 貫穿全書的是林教授「臺灣是獨立的國家」之強烈意識。 誠如林教授自己寫的感慨:
民族活力所呈顯的激奮,發洩在仇恨的對抗上,實在是台灣文化沒落的致命傷。 (p.365)臺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概念以及信念,並不必然要建立在仇恨上, 也不是因為臺灣人的「中國意識」阻止了臺灣意識的存在。 最近這兩年的政治口號之一是「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 就算這句話成立,也不等於鬥倒了國民黨之後,臺灣就會好。 這句話本身是否成立?可能也不必進行太多的辯論, 因為國民黨眼看就要倒了,臺灣到時候好還是不好?等著瞧就知道。
這整本書字裡行間盡情發洩的「恨」,是那麼的清晰。 只希望這本書真的能讓林教授把累積了一甲子的塊壘,一次吐個痛快。 當我讀到林茂生教授的故事,以及從他博士論文引述出來的文字, 真的感到心痛,也許就稍稍體會了林教授以及臺灣知識份子的「恨」。 書裡寫的一句話,在我剛到中央大學任教的那一年, 就由陳建隆教授說給我聽了:「臺灣並不是沒有人才,而是在二二八全被殺光了。」 「寬恕」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沒有要求受害人「寬恕」的權力, 甚至現在說「寬恕」反而是一種褻瀆。 仇恨,肯定使這本書變得沈重,但是並不能使它變得鄭重。 像林教授這樣一位優秀知識份子的活力與激奮,消耗在仇恨的對抗上, 如此之可惜,怎不讓人欷噓感歎?
這本書並沒有提起讓我思考教育的課題,倒是讓我花了好幾天思考另一個問題: 假如是我的身上背負著這樣的仇恨,我要如何自處?我會產生怎樣的意識? 後來,我發覺根本無法回答這個假設性的問題,甚至,思考這個問題的本身, 都是對受害者的侮辱,是我自己的道德敗壞。 可是,我又不能不思考,同為臺灣的住民們,也不得不思考。怎麼辦呢? 我沒有辦法,只能感謝自己的幸運: 感謝我沒有生就背負這種仇恨的身世,我沒有智慧也沒有道德, 能夠活過沒有仇恨的大半生,純粹就只是幸運。 而這種幸運,沒有人可以謝,就只能謝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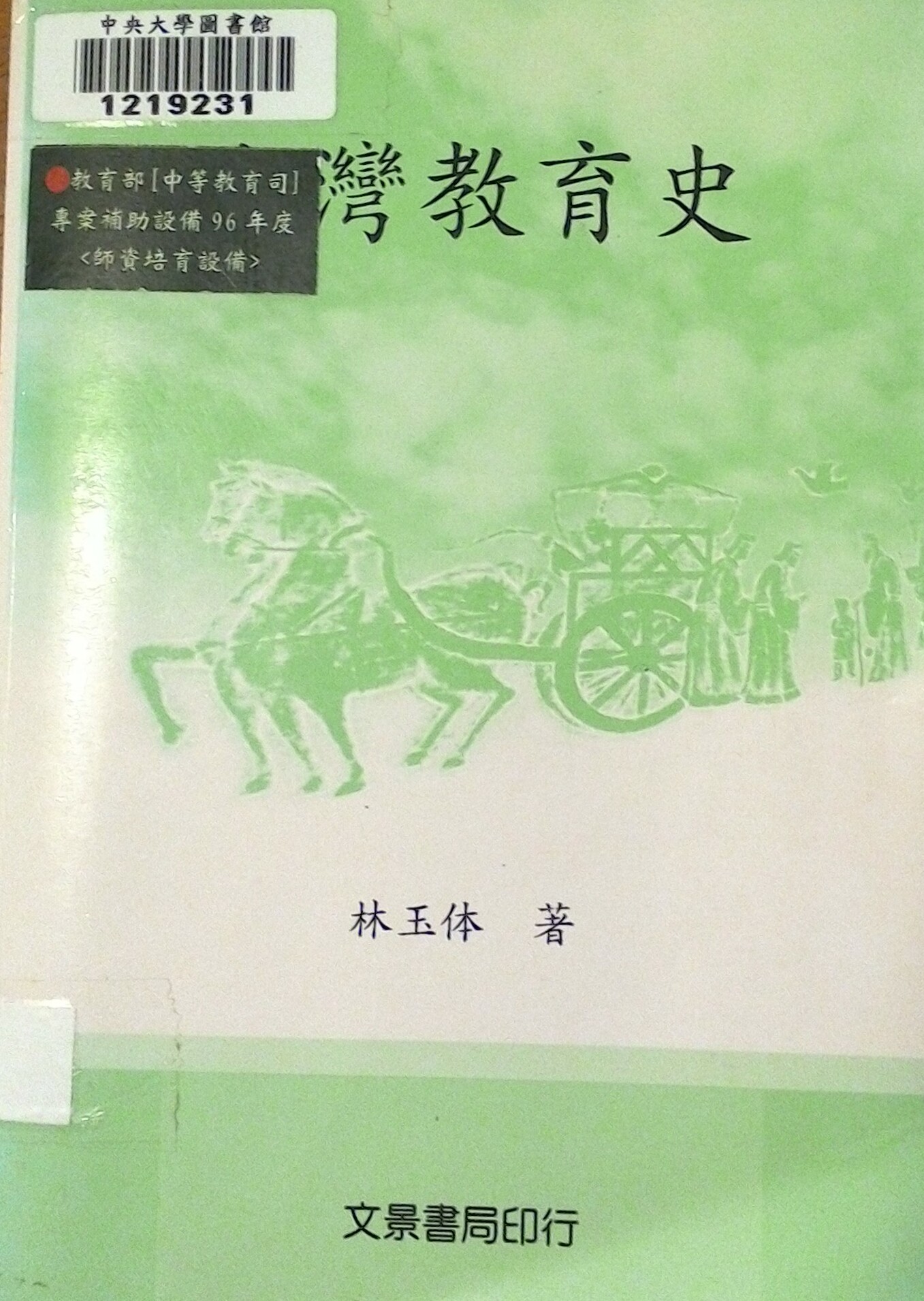 不知道林教授看過這本書的封面沒有?
也不知道其他版次的封面是否跟我這本中央大學圖書館裡的一樣?
我這本書的封面圖像,是相當中國風的孔子周遊列國浮雕版畫。
這一幅圖,平衡了書裡文字所傳遞的激烈意識。
它似乎在不落文字地訴說著,中國或者中華文化,畢竟是台灣文化的底蘊。
不知道林教授看過這本書的封面沒有?
也不知道其他版次的封面是否跟我這本中央大學圖書館裡的一樣?
我這本書的封面圖像,是相當中國風的孔子周遊列國浮雕版畫。
這一幅圖,平衡了書裡文字所傳遞的激烈意識。
它似乎在不落文字地訴說著,中國或者中華文化,畢竟是台灣文化的底蘊。
這本書的第二個可惜之處,是林教授反覆以「民族」本位呼籲臺灣的「本土」意識。 可惜之一是,臺灣住民的「民族」定位為何?可能不容易論述也不容易在人心中落實。 可惜之二是,「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的概念,雖然最近在各國民主政治之中, 以被稱為「民粹」的形式而再度浮現,但那只是在民主制度中獲得權力的形式與手段, 並不是真正的民族意識。林教授是一位真誠的學者,他流露的愛與恨,都是真誠的, 所以他寫的「民族」並不是政客奪權的那種形式與手段,而是真正的民族意識。 這是我感覺可惜的原因。
這本書的第三個可惜之處,是全書已經清楚地結論一個事實: 臺灣的最近一整個世紀,日本帝國的「同化教育」與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 恰好各佔一半。凡統治過的,必留下痕跡;總是有人痛恨,有人緬懷。 正如我從劉廣定教授那裡聽到的名言: 關於人的事情,任何命題和它的逆命題,都同時正確。 我完全相信林教授以下這句話所言不虛:
不少人一聽「中華民國」即起反感與噁心。 (p.366)但是林教授應當不至於否認,擁有這句話另一面情緒的人,也不在少數。 哪一種人多?哪一種人才「正確」?絕不是重點。 重點是,那些過去的統治者造成的事實,不是我們任何人因為愛或者因為恨而能消除的, 臺灣自己的意識,社會意識也好,國家意識也好, 只能從那兩個各半世紀累積的事實裡建立起來, 而不能靠著毀滅那兩個各半世紀累積的事實來肯定自我。 不能只是毀滅與解構,而誤以為當一切都破除了解滅了, 臺灣的純淨本體就會自動從清除掉的廢墟中顯露出來。 萬一當一切都被拆光解盡之後,才發現裡面什麼也沒有,該怎麼辦? 當然這個假設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因為就連一個人的過去都不可能拆光解盡了, 更何況是整個社會呢?
因此,我認為可惜的是, 林教授明明已經以學者的神智,明確分析了兩個各半世紀的統治者, 透過教育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做的種種滿足其自身利益的措施, 卻因為個人的愛恨,對日本帝國那一半隱惡而揚善, 對國民黨這一半則隱善而揚惡,彷彿凡是曾經被後面這半個世紀傳頌過的理念, 全都要拔除毀滅似的。過去既成的事實,不論多麼地不堪,都是我們共同的繼承。 我們繼承的,既可以是資產,也可以是負債,端看我們怎樣運用它。 這本書只顧著發洩仇恨,卻沒有發揮學者的能力與影響力, 帶領我們大家想一想,怎樣善用這筆繼承的既成事實,使它們盡量成為資產, 成為我們建立台灣本土意識的出發點。
p.42ff 對漢文化的「教育」有個概括的描述。
劉銘傳之前,台灣與中國一樣,一般文教,有官學與鄉學之分,前者是官方所辦, 後者則為民間興設。官學有府儒學縣儒學、書院、義學(或稱義塾)四種; 鄉學則有社學及民學(通稱書房)。所有這些較有形的教育機構, 設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參加科舉。後來 1887 年(光緒 11 年)建省之後,或說在劉銘傳主政期間(1885--1891)
創辦新式學堂,聘英國之 Hating 及丹麥之 Pumnllin 為教習,課程增加了外文、 算術、理化、史地和測繪。劉銘傳在位極短,這樣的新式學堂很難想像能發揮什麼實際的作用, 甚至不知道它在歷史上有多少被討論的價值?
林教授說中國傳統體制裡的
教育機構設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參加科舉。(p.42)雖不中亦不遠矣。普通的識字或算術學習,多是家傳或者「在職」培訓, 並不必到學校去。去學校,或者說「上學」,基本目的只有一個:參加科舉考試。 日本統治之初期,臺灣人還是可以到中國去參加科舉,但是數量變得極少, 而且沒多久民國創建,也就不再有科舉可考了。 日本設置公學校(相當於小學),是政府牧民的管道之一, 其目的當然不再是為了中國的科舉。日本統治前的民學,也就是「書房」, 就不再有生源,理論上應該關門大吉才是。其實不然, 這個民間興學的傳統被保存著,而在這個社群中積存的資源和能量也被保存下來, 不知不覺中發展成為另一條產業鏈:補習班。 科舉已經消失了一百年,可是,如張鎮華教授說的,我國「以考試立國」的傳統, 卻一直延續到今天,盤據在我們的教育系統的最關鍵位置上。
中國的傳統思想以及「孔門」的儒學主張,今天看來當然有不宜之處。 但是林教授說
孔門學說又有極強烈的反智色彩,知識無用論是基調,泛道德主義橫行。(p.43)年輕人對孔子有這樣的偏見,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年輕人本來就傾向於反抗權威。 可是,一位年過六十的知識份子,還寫出如此單薄觀點的評述,實在是可惜了。
林教授認為「黨化教育」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軍訓課。 我個人對軍訓課的印象並不深刻,雖然它從來不曾被借去執行數學或英文課, 教官總是認真地照表操課,每回段考也有這門考科,但是真的沒留下什麼印象。 就課程設計的理念而言,我也不贊成軍訓課。 可是,林教授駁斥軍訓課的邏輯相當「經典」, 足以當作邏輯思維或寫作課程的一則範例:
如果軍訓課程包括了「思想、人格、及精神」之培育, 那也等於代表了全部的教育。 要是說軍訓課就是全部的教育, 或甚至說全部的教育課程只需軍訓一科即已足夠, 這種說法也不為過。(p.223)
教育向來是私領域的事,為了滿足個人或家族的需求(或樂趣)而從事。 伴隨著經濟活動的轉型,政府為了提高「國家」競爭力,也為了管理, 逐漸發展出公部門的教育政策與設施。 前者(私領域)的教育可視為 Learning,後者(公部門)的教育則是 Schooling。 Learning is free. Schooling costs。Learning 是自由的、自主的, 但 Schooling 是制約的、被動的。 私領域的教育目的,和公部門的並不一致,如果處理不當,甚至可能是互相衝突的。 林教授在 p.82 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日本執政者擔心,臺灣人會認為接受公學校教育是與統治者結合而成為升官發財的跳板, ... 但日本政府希望(入公學校)量的增加以外,還更應該讓公學校畢業生能接受家長原有的經濟及社會職分及地位。 公學校給年青的一代更新的技巧,能夠在就業上更效率。前面寫的都是「殖民教育」的觀點,似乎認為那是殖民政府的特殊觀點。 其實不然,假設自己是執政者的立場來仔細想想,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 為什麼要投資教育來創造一批有能力質疑甚至反對自己的人呢? 不論殖民與否,我認為公部門對教育的看法和心思,本質上是一樣的。 對教育現況不滿的人,必須要認清私領域和公部門教育的差異。 而思考「教育改革」的人,則不但要認清它們的差異, 還要設法盡量讓它們相輔相成。任期從1910年8月到1915年11月的臺灣民政長官內田嘉吉 (Uchida Kakichi, 1864--1933) 於 1915 年 5 月的地方官員眾會中,直率地道出上述的擔心。 當時台灣人熱切的希望接受公學校以上的中等教育,但他認為 ... 臺灣人只要接受職業教育即可,提供學生實際的工作技巧, 好讓臺灣人賺更多錢,過一個幸福的生活。
第 100 頁引述美國記者 Julean Arnold 於 1908 年的報導, 讓人可以想像「新式學校」帶給臺灣「家長」的困惑, 對於教育之目的的想法,從那時候才開始在很少數人的心目中開始改變。
(除了體育以外)音樂科也深為臺灣學生所喜愛。臺灣小孩音感之佳, 不下於日本學童,甚至超過;學童興沖沖地走入音樂教室, 透過音樂教學,也可以進行語言教學。 不過一般而言,家長比子女較不喜音樂及體育, 老一輩的寧可讓孩子多唸書,少上這些娛樂活動。
p.122ff 引述了林茂生博士在 1927 年的學位論文裡,對日本殖民教育的評論。
近代教育的特質,在於把教育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以實現另一個和被教育者關係遙遠的目的。 --林茂生 1927 (p.122)這麼「浪漫」而且「進步」的觀念,想必是從杜威那裡學來的。 我發現林茂生教授的么女為他翻譯了這本博士論文,已經從中大圖書館借回來了, 所以不在這裡多做紀錄。
第五章「臺灣意識」的主角是「台灣文化協會」。
中國革命、俄羅斯共產主義革命、共產國際活動、及日本無政府主義等, 也間接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 有兩位靈魂人物, 一是台中的林獻堂,一是宜蘭的蔣渭水。 (p.131)文化協會的《會報》於 1921 年(大正 10 年)11 月 28 日創刊。 林教授傳述文化協會在全台各地舉辦研習, 活動最盛的那兩年(昭和二年,西元 1927,及次年)一共舉辦 448 場,
內容皆攻擊資本主義制度及帝國主義之侵略,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的解放 (p.144)可見「台灣文化協會」屬於共產國際的成分似乎居多,而他們的行為模式, 流傳至今而依然讓人感到面熟:
當時各地經濟界也有勞資糾紛,佃農挺身而出,是文化協會大展身手的場所, 竭盡所能的介入、指導,使紛爭惡化,其中以新竹騷擾及台南廢墓地問題的行動最為典型。 (p.144)「使紛爭惡化」,好一個言簡意賅的註腳。
1925 年 8 月王受祿在文化協會夏季研習會講了一段話:
本島人負有三種負擔,那就是漢文、臺灣話、日本話的負擔, 因此文化的發達就遲慢了。 倘若沒有國語(指日語)、漢文,只有臺灣話,那麼進步就非常得快。(p.140)那些研習會都有「煽動」的共通性,而且講者多半是剛獲得知識的熱血青年, 所以論述難免過於疏淺;但是,以上論點倒是非常值得警惕。 今天的國民,自動把日語的負擔改成了英語的負擔, 而(公部門)教育制度又增列了「母語」或者「新住民語」, 使得學童的負擔絕不亞於王受祿先進那個時代的情況, 而一般學童對臺灣話的嫻熟程度,以及臺灣話本身的語彙範圍, 則很可能不及王受祿的那個時代。 萬一王受祿的預言是正確的,那麼如今臺灣「文化的發達」是不是更遲慢了呢?
林教授書裡對林獻堂著墨不多,似乎比較推崇蔣渭水。他在 p.147 寫道
「上醫醫國」的蔣渭水,以醫學立場,道出 1920 年代臺灣人的病症, 可以與日本政要後籐新平觀察臺灣人之「怕死、要錢、愛面子」相互作個對照。 蔣渭水看到的是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 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罔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 只圖眼前小利。 (白成枝編〈先烈蔣渭水傳略〉《蔣渭水遺集》1950,p.194。)
公部門的教育就是政治的延伸,
政治不正常,教育休想上軌道。(p.148)這是全書我最最贊成的一句話。臺灣所有的「教改」亂象都是政治不正常造成的, 台灣所有的(公部門)教育問題,都是政治問題。 只能說,幸好,數學領域受波及的比較少,但是覆巢之下無完卵, 數學和自然科學,到最後仍然休想置身事外。 君不見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師(其實社會領域的教師也是)哀嚎的困境都一樣嗎? 然而,當公部門的教育失能,只能期盼私領域的教育發揮功能, 而家庭的社經地位就在這時候產生了它的影響力。
第 359 頁列出了當年「教改」的全體委員名單,次頁記載哪些人退出,哪些人增補。 當時「教改」才剛開始不久,林教授以其教育的專業,已經感到不妥, 可是似乎不便明白地寫出來,對李遠哲和李登輝都是輕輕碰一下,欲言又止。 他對「教改」沒有直接的評論,卻在全書的最末,留下這樣一份名單, 意有何指?真的是耐人尋味。
【後記】
我在 2016 年 9 月號 (No.66)〈通識在線〉期刊上巧遇林玉体教授。 台北市立大學但昭偉教授引述林玉体教授寫在《教育哲學--隱喻篇》第一章 「教育是...教育似...」裡面的話
在經驗界中,(光陰似)箭及(日月如)梭在古代的支那社會裡都有『速』意, 但如放在今日,已不適用了,因有比光速還快的。 (p.43)然後寫了大約一百字的評論,認為林師「的文字應該可以更謹慎才對」。 我想,放在今日的不當隱喻,例子可多了,不知為何扯到「光速」? 忍不住補兩個我最喜歡的例子:「朝發夕至」不知現在該用作快的隱喻還是慢的隱喻呢? 「過江之鯽」不知現在該用作多的隱喻還是少的隱喻呢?同期刊載了林玉体教授的回應:
附帶一提,B. Russell 認為,logic 及 mathematics 才是絕對, 其他的 sciences 不用說 social sciences 連 natural sciences(如 physics) 都只是相對。因之如電光之速度最「快」都不必然是「定論」。 概率 (probabilities) 高低而已。 「心思」不是比光更快嗎?當我「心」想及美國時, 一想即到美國,電或光呢?至少還遲些! (p.45)這位老先生實在太可愛了,而〈通識在線〉還是來文照登,我覺得也很可愛。 羅素在 1903 年出版的書裡提出前面引述的主張,當時 Gödel 還沒提出他的不完備定理。 如今,因為不完備定理,我們對數學和邏輯的認識略有不同了。 我還要再維護羅素一下:他應該是具備「科學理論非恆真」之概念的, 但應該不是用「相對」來說的,他應該也沒說過關於「概率高低而已」的觀念。